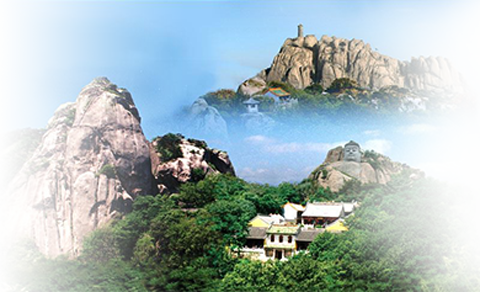《传习录》中古代哲学思想
对现代司法的启示
□刘月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王阳明心学代表著作,《传习录》记载了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书信集。这些语录、书信所包含的阳明心学哲学思想,不仅为世人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而且蕴藏着丰厚、深沉的司法智慧。 法官倘若能在修身、断案、释法明理中对此进行学习善用,可以成为预防司法腐败、提升公众司法公正感知度、发挥司法教化功用的一剂传统文化良方。
“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这三个命题相辅相成,共同架构起阳明心学的哲学体系。“心即理”,即“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指万事万物之理本就天然藏于内心之中。每个人都有一颗光明本心,良知就在光明本心之中,要在光明本心的指引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同时指明法官应以擦亮光明本心为努力方向,应以符合公众良知为自由裁量权运用方向,应以唤醒当事人及社会大众心中沉睡的良知以及被遗忘的传统美德为释法明理方向。“知行合一”即事上用功,侧重在与外在世界的互动中进行实践,是主体自觉到良知并将良知完全开显出来,并按照良知的要求去处理事物的过程,是从满足主体的自我成就感出发推动道德实践的过程。“致良知”侧重心上磨练,人人都有良知,不过受现实情况或不良刺激,在生存过程中会违背良知,导致良知被遮蔽,不能发挥它的能量。心上磨练是一个提高人生境界、道德情感、理性自觉和道德意志的认知过程。“知行合一”和“ 致良知” 为法官加强自我约束、 遵循司法良知、教化社会公众提供了以下具体路径:
时刻省察克己,以无私之心公正清廉断案。
相对于其它职业,社会对法官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要求其不为物欲蒙蔽,不因人情所动,不局限于自己的私心。尽管脱去法袍之后,法官只是一个在尘世中生活的普通人,但法官品行、道德境界必然应高于普通人,这是法官职责所决定的。“刑事审判决定着人的生命和自由,商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决定重大利益的归属和身份关系的变化,行政审判关涉着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分配”,而法官就掌握着这种予夺的权力。
从自我监督层面,良知就像内心的岗哨,监视着司法者的行为,防止司法者触破原则底线。法官大都满腹经纶,专业知识水平很高,但有一少部分人利欲熏心,知法犯法,不仅能发挥自己作为司法工作者的社会价值,反而损害了法院名声,污染了社会风气,许多法院人兢兢业业建立起的司法威信也随之付出东流。对于法官来说,外在的司法风险防范系统有利于自身规矩处事,内在的良知则能发自本心的指引自己慎独,不追求违法利益,表里如一,守住思想底线。法官需要并应该通过良知修养,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与审判水平,成为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也只有通过法官个体境界的不断提升,法院文化的养成才成为可能。
挖掘司法良知,以司法良知指引自由裁量权运用。
当下,人民法院为定分止争、维护社会秩序、树立司法权威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不菲成效。但仍有部分当事人不接受、不认可裁判文书,采取上访、闹访等方式讨公道,社会公众也对诸多案件的审理存在质疑,司法权威仍待加固。究其原因,乃是法官传递的公平正义价值观未被社会大众认可。
案件审理有三个不同的境界:单纯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司法民工、能处理疑难司法案件的司法工匠与遵循良知引导的司法大师。 司法民工单纯付出精力,像自动售货机一般,一个口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个口输出司法判决,机械运行。司法工匠掌握了法律理解和适用的技巧,面对复杂的不能机械化处理的案件可依靠其深厚的理论素养解决。司法大师则敬重天理人伦,遵循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尊重人性,以良知考量公平正义,指导裁判行为。可见,法律思维是法官以自身专业技术实现司法正义的途径和形式,而司法良知则是能确保审判得当的灵魂和根基,对案件的判断既要遵循法律,也应不忘听从良知的判断、人性的呼唤。
弘扬传统美德,以释法明理发挥司法教化功用。
教化作为中国古代司法的一项重要功能,在当今也同样适用。中国司法传统的一大特点是重视司法的教化作用,重视良知的传递。在中国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体制下,地方行政长官兼领司法权,道德教化不仅是其行政责任,也是其司法目标。刑罚通过制裁力量阻却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的行为,与此同时,也通过内含的道德精神对当事人和旁观者发挥教育感化的功能。
现代社会,许多纠纷因物质利益而起,很多案件的当事人陷入金钱利益的漩涡不能自拔。法官以良知为价值指引,追求实质正义,进行价值衡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积极释法明理,对当事人及社会大众来说,毋宁是接受一场道德上的洗礼。
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就应学习中国哲学,运用中国哲学,用中国哲学解决中国司法问题,走中国特色的司法审判道路。